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摘 要:數字化教材是構建智慧課堂的重要內容,支持著信息技術與課程教學的整合,推動著課程教學方式的變革。研究基于文化歷史活動理論,分別從學生和教師視角構建了數字化教材的使用模型。從學生視角出發,為推動自主化、個性化的學習,學生需要掌握數字化教材使用策略,開展學習活動的全方位記錄;從教師視角出發,為推動數字化、智慧化的教學,教師需要加強對學生的過程性評價,構建教學互動的智慧交流圈,為實現智慧課堂提供條件。
關鍵詞:數字化教材 文化歷史活動理論 智慧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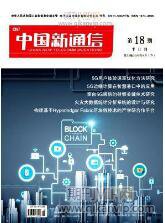
目前,我國已從數字化教育建設階段轉入智慧教育階段,而教育信息化目標的實現,則需要借助信息化教學環境去變革傳統課堂教學結構[1]。新一代信息技術打造的智慧課堂,能為學生帶來智能、高效、有趣的學習體驗,而這種體驗的生成離不開信息技術支持下課堂教學的變革。
數字化教材作為智慧課堂實施的重要平臺,其開發與實施成為了近年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我國從2000年“校校通”項目開始,首次把紙質教材搬到網絡;2002年人教社研發手持式數字化教材在9省10所學校開展如何使用數字化教材的實驗;2012年人教社明確提出“數字教材”的概念,并啟動第二代人教數字教材的設計和開發。至今,我國數字化教材已歷經二十年的發展。同時,國外數字教材也在不斷發展。以美國為例,截至2020年8月,美國專業教材編寫團隊開發的“發現教育(DISCOVER EDUCATION)”數字化教材已經服務了超過140多個國家、近五百萬教育工作者和五千多萬學生[2]。數字化教材經過多年的探索、研究、實驗,已真正走進了課堂,走到了教師和學生面前。
數字化教材已經順利實現了由教科書電子化向多媒體數字化的過渡,當前正在朝向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為基礎的數字化平臺發展。區別于電子書、電子課本和電子書包,數字化教材既是一種數字化的教學系統,也是一種立體化的學習支持平臺。它有機整合了不同形態的資源,同時可以滿足多種學習需求,支持反復使用,實現及時通信、共享資源、動態交互的目的[3]。相較于傳統教材,數字化教材拓展了學生的學習資源,全方位記錄學生的學習過程。它不僅能成為教師數字化教學的有效助手,更能協助教師搭建開放活躍的智慧交流圈。數字化教材的有效使用提升了學生的信息素養、基礎批判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創造力[4],而且對學習成績有正面效應[5]。但也有研究表明,數字化教材和傳統教材對學習結果的影響并無顯著差異[6],甚至前者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7]。數字化教材使用結果的矛盾表明其在使用過程中存在問題。從紙質教材到數字教材的轉變,不僅是教材選用的轉變,更是教育理論當中知識觀和學習理論的發展[8]。如何使用數字化教材,將數字化教材有效融入智慧課堂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數字化教材使用模型構建
1.文化歷史活動理論模型
活動理論揭示了一般的活動結構與關系,而數字化教材的使用(即學生利用數字化教材學習)是一種具體的活動,它符合活動的一般結構,但又有其特殊性。數字化教材作為活動工具,能夠在人(主體)和他們所追求的目標(例如理解事物或者完成任務)之間起中介作用[9]。但它同時也能自主地控制、調節和推進活動進程,對活動進程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使其在工具性基礎上擁有了活動客體的價值。通過三角示意圖(如圖1),文化歷史活動理論將主體、客體和工具之間的關系清晰展現。
文化歷史活動理論起源于辯證唯物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由維果斯基正式提出,歷經三代發展[10]。第一代活動理論以維果斯基為代表,他強調個體不是直接對環境作出反應,而是借助文化工具作為中介來實現目標。第二代活動理論由他的學生盧瑞亞和列昂節夫完善,提出了活動的層級結構,強調共同體需要在宏觀層面分析活動,引進了規則、共同體和分工,凸顯了個體和共同體的互動。第三代活動理論以恩格斯托姆為代表,突出活動的社會性,提出“學習者集體”和“高級學習網絡”的概念,以相互作用的多種活動系統作為分析單位,構建了六要素分析模型(如圖2),此模型也是當今最成熟、運用最廣的文化歷史活動理論模型。第三代活動理論注重活動系統的多重聲音,強調矛盾在活動中的重要作用,并鼓勵成員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反思,推動整個系統產生質的變化[11]。在教育教學的過程中,活動理論提供的歷史文化方法能有效分析植根于情境的動態問題。在智慧課堂當中,研究者可以通過此理論分析作為中介的數字化教材的使用模型和運用策略。
2.學生視角的數字化教材使用模型
文化歷史活動理論指出人類活動是以工具為中介來調節主體與環境之間的交互,且工具影響人的外部行為和智力發展。作為一種策略性工具,數字化教材豐富了學生的學習資源和學習方法,讓學生能隨時、隨地進行趣味化、自主化的學習。傳統的紙質教材承載內容有限,無法拓展額外知識,且局限于特定時空,需要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學習。相比之下,數字化教材承載了海量的學習內容,支持豐富的媒體資源形式。此外,數字化教材打破了學習的時空限制,讓學生能夠隨時隨地進行自主化學習。例如,學生可以在課后利用數字化教材重新學習不懂的知識,搜索自己感興趣的內容。當學生掌握了數字化教材的使用方法和運用策略,便能在相關任務要求下進行有目的、有方法的自主性學習。在自主性學習模型當中,數字化教材作為工具性存在促進了學生自主性學習的發生,同時也讓學習活動共同體成為了可能(如圖3)。它將師生聯結成共同體,讓自主性學習既能在個體的探究下發展,又能在集體的指引下成長。
作為活動理論的分析單位,活動能夠將學習者的思維過程外顯,及時調整學生的學習活動,有效實現學習內容的建構[12]。實時、準確記錄學生的學習活動是對個體的深入了解。數字化教材作為學習活動系統的中介,它不僅能為學生的學習過程提供全方位記錄,更能為其提供個性化學習指導。從學習活動系統出發,數字化教材貫穿于課前預習、課堂參與、課后評價;從個體出發,其涉及任務的查看、完成和反思。在目的化、流程化、周期化的學習過程中,數字化教材實時記錄了學生的學習動態,例如學習筆記、搜索記錄、學習時長等學習痕跡。學習過程的全方位展示和分析,不僅幫助學習者了解自身發展水平,更能幫助其回顧探究過程,實現思維的有效進階。在大數據和算法的支持下,數字化教材也能根據學習者的需求推送專屬資源,有力推動學生的個性化學習。在個性化學習模型中,數字化教材通過外顯學習者的思維和實踐過程,幫助學習者了解學習情況,構建“數字化肖像”,為個性化學習打下基礎(如圖4)。
推薦閱讀:數字化管理師如何發表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