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術指導 符合學術規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 保證專業,沒有后顧之憂
摘要:生產性服務業與傳統制造業的融合發展,是推動傳統制造業改造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本文利用世界投入產出表測算了中國和OECD國家2000-2014年生產性服務業與傳統制造業融合程度,采用工具變量和GMM估計方法,重點就中美之間的指標進行了比較,并根據跨國面板數據測算了融合度指標對各國勞動生產率的影響。研究發現,與美國融合度指標相比,中國生產性服務業與傳統制造業的融合程度明顯偏低;在生產性服務業的細分領域,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同樣明顯,美國生產性服務業對中國傳統制造業的融合度指數要顯著高于中國對美國的融合度指數;生產性服務業與傳統制造業的融合發展能夠明顯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改善。據此,筆者提出了支持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壯大,促進與傳統制造業融合發展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生產性服務業;傳統制造業;產業融合;勞動生產率;國際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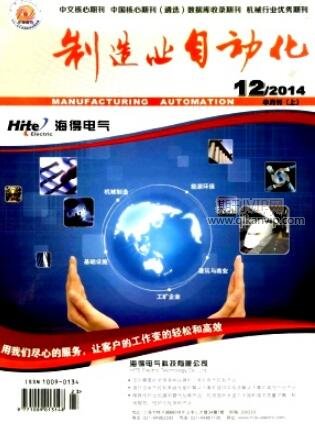
一、引言
當前,高質量發展日益成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改進升級傳統制造業是實現高質量發展戰略的重要方面。生產性服務業與傳統制造業融合互動推動產業升級、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經。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性已經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國發〔2014〕26號)明確指出,生產性服務業涉及農業、工業等產業多個環節,具有專業性強、創新活躍、產業融合度高、帶動作用顯著等特點,是全球產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是向結構調整要動力、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重大措施,既可以有效激發內需潛力、帶動擴大社會就業、持續改善人民生活,又有利于引領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提升。
在學術界,生產性服務業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的重要作用同樣引起了廣泛關注。夏杰長和倪紅福[1]認為,服務業和工業自身特點發生了根本變化,服務業與工業的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對生產性服務業的范圍進行界定后,Zheng和Sally[2]認為,作為經濟“粘合劑”,生產性服務業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它改變了服務產品的內容和性質以及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服務越來越多地作為一種軟生產資料進入生產領域,使生產性服務業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對此,王如忠和郭澄澄[3]通過對北京、天津和上海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增加值樣本數據的比較和價值型投入產出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發揮生產性服務業對制造業的引領作用,不僅有利于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發展,也是當前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提升產業發展能級、提高產業綜合競爭力的重要內容。郝一帆和王征兵等[4]研究發現,人世以來,生產性服務業顯著地促進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提升,已成為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就對城市的影響而言,金曉雨[5]認為,在中國城市體系下,制造業的內生分布使大城市相比小城市對生產性服務業有更高的需求。大城市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通過前后向關聯提升了城市生產率。Kozar[5]在對美國制造業的轉移過程進行研究后發現,知識密集型商業服務通過使用專業知識和創新技術,處于現代經濟增長的最前沿,而商業服務業的復雜性使其日益成為知識型大都市經濟的主導驅動力。
針對生產性服務業究竟是如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唐曉華等[7]通過采用灰色GM(1,N)模型測度了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演化發展程度,發現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良好協同發展對制造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具有顯著的促進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二者的融合發展來實現的。制造業投入服務化反映了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程度,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推動力。劉維剛和倪紅福[8]利用匹配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和全球投入產出表數據,將制造業投入服務化作為融合指標,認為二者的融合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推動力。Hemila和Vilko[9]、Li和Gao[10]、周靜[11]與李超和張哲[12]將研究的切入點從二者的融合角度展開,認為生產性服務業通過與制造業藕合,不僅促進了自身發展,而且提升了制造業生產效率,促進了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攀升。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數據,對生產性服務業通過融合互動促進制造業生產率的提升等進行了分析。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利用國際數據尤其是國際比較方面的研究尚存真空,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切入點。本文的創新和邊際貢獻主要在于:一是利用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WIOD)中2000-2014年的世界投入產出表,詳細測算了世界范圍內主要經濟體在此期間的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融合度,為本文進行跨國比較研究提供了數據支撐,并重點對中美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分析;二是在實證環節,利用OECD數據對產業融合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進行跨國面板實證研究,填補了國內同類研究的空白;三是在回歸模型的選擇上,采用工具變量和GMM估計方法,有效地降低了模型的內生性,使結果更可信。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的提出
隨著服務經濟時代的全面來臨,服務業和制造業之間的產業邊界日益模糊。智能制造、柔性生產、制造業的服務化和服務型制造早已司空見慣。宣燁[”]認為,就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演化歷程來看,發達經濟體的實踐經驗表明,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的關系經歷了從高度依附轉向相互支撐,進而轉向發展引領的演進過程。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全球生產的日益碎片化。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基于成本的考量,將附加值較低的制造環節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自己則占據并專注于設計、研發、品牌、銷售等附加值較高的環節。由此形成了一個聯系日益密切的全球價值鏈,并深刻地改寫了以制成品貿易為主的全球貿易格局。在這種分工體系下,發達國家占據著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而發展中國家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制造環節。國家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是否掌握全球價值鏈的話語權,而這種話語權又常常是通過發達的服務業,尤其是生產設計、金融、商務咨詢、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來實現的。
推薦閱讀:制造業自動化是北大核心期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