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VIP學(xué)術(shù)指導(dǎo) 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zhì) 保證專業(yè),沒有后顧之憂
期刊VIP學(xué)術(shù)指導(dǎo) 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和道德
保障品質(zhì) 保證專業(yè),沒有后顧之憂
來源:期刊VIP網(wǎng)所屬分類:綜合論文時(shí)間:瀏覽:次
摘 要: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中,政府需要與企業(yè)、民眾、社會(huì)組織進(jìn)行協(xié)商合作,以分散和化解風(fēng)險(xiǎn)。對(duì)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分析發(fā)現(xiàn),在集體行動(dòng)的視域下,公共危機(jī)中民眾的秩序維護(hù)型自組織具有復(fù)制、嵌入、相變?nèi)N機(jī)制。復(fù)制式、嵌入式、相變式自組織的任務(wù)性均很強(qiáng),相變式自組織的結(jié)構(gòu)性最強(qiáng),嵌入式自組織的結(jié)構(gòu)性最弱。它們顯著區(qū)別于黨政組織的強(qiáng)制機(jī)制、企業(yè)組織的交換機(jī)制,也與非政府組織的志愿機(jī)制不完全相同。這些自組織對(duì)于解決公共危機(jī)問題、有效動(dòng)員組織民眾、強(qiáng)化政府元治理能力意義重大,同時(shí)也受到開放性、規(guī)則性、狀態(tài)性、反饋性等約束。面對(duì)挑戰(zhàn),我們既要通過空間讓渡和規(guī)則建設(shè)來提升社會(huì)的自組織化,也要強(qiáng)化個(gè)人的責(zé)任性,通過提升民眾的素養(yǎng)與能力,讓個(gè)體承擔(dān)更多社會(huì)責(zé)任。
關(guān)鍵詞:自組織;公共危機(jī);危機(jī)管理;新冠肺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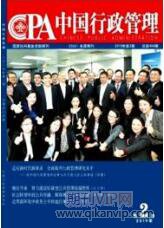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xiàn)綜述
新冠肺炎是典型的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它給社會(huì)系統(tǒng)造成了各種失序和紊亂。我們看到,疫情發(fā)生后,大量民眾/志愿者通過各種自組織方式進(jìn)行著物資采購和運(yùn)送、服務(wù)醫(yī)護(hù)、保障患者、關(guān)懷弱勢(shì)群體等活動(dòng),為抗疫做出了巨大貢獻(xiàn)。
實(shí)際上,在公共危機(jī)發(fā)生后,民眾自主參與危機(jī)應(yīng)對(duì)的方式有兩類:個(gè)體行動(dòng)與集體行動(dòng)。個(gè)體行動(dòng)能夠?yàn)閼?yīng)對(duì)危機(jī)增加人力、財(cái)力、物力資源,能第一時(shí)間提供現(xiàn)場(chǎng)救援,給組織化救援創(chuàng)造緩沖時(shí)間[1]。但危機(jī)中民眾的行為具有高度的復(fù)雜性和不確定性,故個(gè)體化的行動(dòng)也會(huì)降低應(yīng)急資源的規(guī)模效應(yīng)和利用效率,尤其是未經(jīng)專業(yè)訓(xùn)練的大量碎片化個(gè)體,會(huì)導(dǎo)致危機(jī)應(yīng)對(duì)缺乏整體性而出現(xiàn)無序和低效[2]。因此,我們應(yīng)辯證看待危機(jī)中的個(gè)體行動(dòng),揚(yáng)長避短。邁克爾·布蘭德(Michael W.Brand)提出了三種策略:拒絕參與;臨時(shí)動(dòng)員;平時(shí)就將其納入應(yīng)急體系中[3]。王宏偉提出,應(yīng)該建立危機(jī)時(shí)的制度安排,進(jìn)行程序化的管理,如設(shè)定志愿者集結(jié)點(diǎn)、通報(bào)信息并進(jìn)行輔導(dǎo)、登記注冊(cè)并進(jìn)行資質(zhì)審查、分配應(yīng)急救援任務(wù)、監(jiān)督任務(wù)完成[1]。
公共危機(jī)中民眾的集體行動(dòng)有兩種路徑:一是加入紅十字會(huì)等災(zāi)害響應(yīng)的正規(guī)組織,即他組織;二是自發(fā)自愿組織起來并開展自我管理,即自組織。目前,學(xué)界對(duì)第一種路徑的研究非常豐富,而對(duì)第二種路徑的研究則相對(duì)不足。克蘭特利和戴恩斯(Quarantelli & Dynes)將危機(jī)中臨時(shí)成立的應(yīng)對(duì)組織命名為“突生組織”,這類組織以一種新的結(jié)構(gòu)執(zhí)行新的任務(wù)[4]。從地位來看,斯托林斯和克蘭特利(Stallings & Quarantelli)指出,公共危機(jī)中民眾的突生組織現(xiàn)象是不可避免的,危機(jī)或?yàn)?zāi)害的發(fā)生必然會(huì)催生民眾結(jié)群[5];張海波基于魯?shù)榈卣鸬陌咐芯堪l(fā)現(xiàn),中國的集權(quán)體制下,災(zāi)害也會(huì)催生民眾的自組織[6]。從功能來看,這種自組織行動(dòng)包括損失評(píng)估與信息傳遞、物資籌集與分發(fā)、矛盾糾紛調(diào)解三種類型[5],或者是救援、動(dòng)員、治安、宣傳等[6]。從特征來看,自組織都是自主發(fā)起、自主籌建、自主治理的組織形態(tài)[7];自組織規(guī)模都較小、存續(xù)時(shí)間都較短,結(jié)構(gòu)臨時(shí)性與成員復(fù)雜性是其典型特征,多數(shù)臨時(shí)自發(fā)類組織會(huì)隨著突發(fā)事件治理行動(dòng)的終止而解散[5]。從動(dòng)因來看,自組織集體行動(dòng)中的個(gè)人動(dòng)機(jī)是復(fù)雜多樣的,往往是基于混合動(dòng)機(jī)之上的意義建構(gòu)[8],弗里茨和馬修森(Fritz & Mathewson)曾將危機(jī)中向?yàn)?zāi)區(qū)匯集的人分為焦慮者、救助者、獵奇者、牟利者[9]。
盡管既有研究取得了較多成果,但依舊存在如下兩點(diǎn)不足。其一,對(duì)危機(jī)中民眾自組織的價(jià)值認(rèn)知不足。既有研究很少專門探討危機(jī)中民眾自組織的價(jià)值,大多將其糅合在危機(jī)中民眾的個(gè)體行動(dòng)和他組織的集體行動(dòng)中。對(duì)其價(jià)值認(rèn)知呈現(xiàn)出碎片化有余系統(tǒng)性不足、否定性有余肯定性不足的特征,這直接導(dǎo)致了危機(jī)應(yīng)對(duì)中對(duì)民眾自組織的忽略甚至拒絕。其二,對(duì)危機(jī)中民眾自組織的機(jī)制認(rèn)知不足。既有文獻(xiàn)對(duì)民眾危機(jī)參與的觀注點(diǎn)主要聚焦在兩端,要么分析個(gè)體,要么分析組織,而對(duì)個(gè)體結(jié)群成為組織的過程分析較少,個(gè)體化的民眾是如何組織起來的,依舊是個(gè)有待打開的黑箱。將民眾自組織的危機(jī)應(yīng)對(duì)與個(gè)體化危機(jī)應(yīng)對(duì)、他組織的危機(jī)應(yīng)對(duì)混同,使得對(duì)自組織的行動(dòng)機(jī)制認(rèn)知不清。
據(jù)此,這里將采用多案例研究法,選取新冠肺炎疫情中民眾自組織的典型案例,探究公共危機(jī)中民眾自組織的機(jī)制,以厘清它與政府組織的行政機(jī)制、企業(yè)組織的市場(chǎng)機(jī)制、非政府組織的志愿機(jī)制的區(qū)別,并分析公共危機(jī)中民眾的自組織行動(dòng)面臨著哪些困境與不足。
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民眾的自組織分析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后,不論是在最初疫情中心的湖北,還是在其他省市,民眾自組織抗疫的案例不勝枚舉。這里根據(jù)典型性、代表性、資料可得性三個(gè)標(biāo)準(zhǔn)選取互聯(lián)網(wǎng)人Yo!群、順豐快遞員汪勇團(tuán)隊(duì)、風(fēng)韻出行醫(yī)護(hù)專車車隊(duì)三個(gè)案例,采用案例深描的方式解析公共危機(jī)中民眾的自組織機(jī)制。本文所用的數(shù)據(jù)、材料主要來自兩個(gè)方面:一是“寫出來”的信源,包括權(quán)威性的媒體報(bào)道、官方文件、新聞發(fā)布會(huì)、社交媒體、情勢(shì)報(bào)告等;二是“說出來”的信源,即通過網(wǎng)絡(luò)、電話等形式對(duì)三個(gè)組織的負(fù)責(zé)人及部分志愿者的深度訪談。
(一)互聯(lián)網(wǎng)人Yo!群
互聯(lián)網(wǎng)人Yo!群(以下簡(jiǎn)稱Yo!群)是由來自騰訊、百度、字節(jié)跳動(dòng)等公司的77位互聯(lián)網(wǎng)人自發(fā)成立的臨時(shí)性的抗疫志愿服務(wù)組織,組織成員的職業(yè)包括產(chǎn)品經(jīng)理、程序員、財(cái)務(wù)、運(yùn)營等。在2020年1月25日至2月1日的六天內(nèi),該組織共對(duì)接及援助醫(yī)院115家,籌集善款48萬多元,捐助各類口罩5.83萬個(gè)、護(hù)目鏡6375個(gè)、各類消毒用品7350瓶。
1.緣起:基于共情的復(fù)制
隨著2020年1月20日鐘南山院士宣布新冠病毒會(huì)人傳人、1月23日武漢開始封城,新冠肺炎疫情成為全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Yo!的微信群里也不斷匯聚著關(guān)于武漢疫情的消息。在群成員圍繞疫情信息的互動(dòng)中,產(chǎn)生了觸發(fā)自組織集體行動(dòng)的序參量——對(duì)災(zāi)難的共情。“大家看到武漢一線醫(yī)生的事情,很動(dòng)容,又很無力。”這種情感共鳴建基于成員對(duì)武漢抗疫資源供求狀況的判斷——嚴(yán)重的物資短缺。在認(rèn)知選擇理論中,認(rèn)知是有選擇性的(選擇性注意、選擇性理解、選擇性記憶),人們會(huì)選擇性地感知那些他們期望和愿意看到的事物。Yo!群成員并沒有去大量收集信息、精確地衡量狀況是否真的嚴(yán)重、嚴(yán)重程度幾何,而只是基于一些點(diǎn)狀的或是片狀的信息做出判斷,即他們選擇相信武漢抗疫物資是極度短缺的。如成員CDP介紹,他是通過微信朋友圈和社交媒體上諸如醫(yī)生吃泡面、醫(yī)院求助等信息了解到疫情一線的醫(yī)護(hù)物資匱乏,基本處于“裸奔”狀態(tài)。
推薦閱讀:公共管理碩士畢業(yè)論文發(fā)表核心期刊嗎